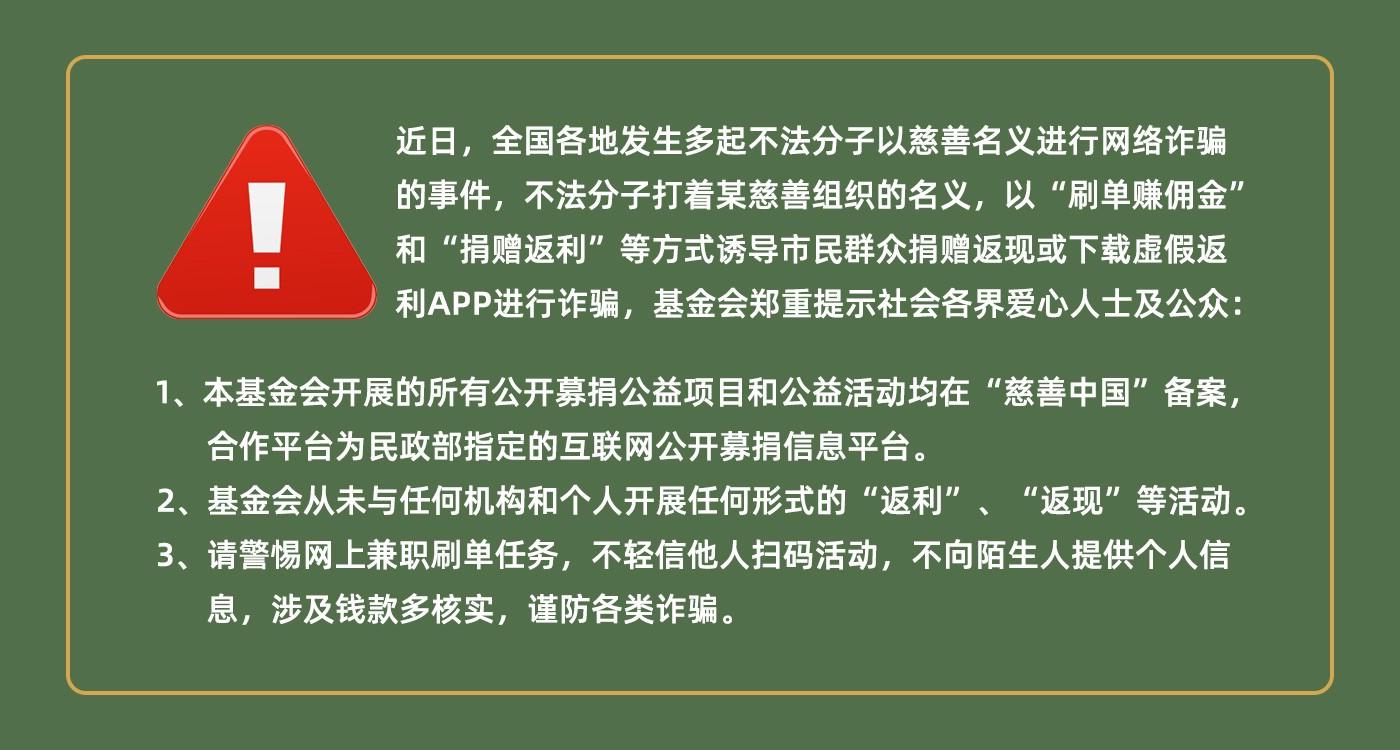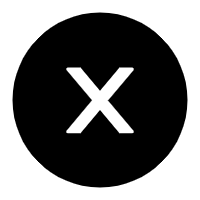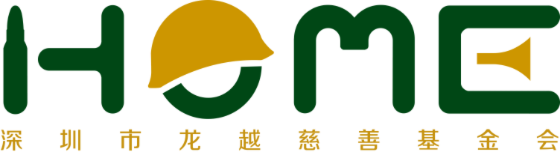引言
75年前,中國(guó)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,曆史不會(huì)忘記那些曾經(jīng)爲國(guó)而戰的英雄。
從1942年春天到1945年年初,爲了抗擊日本法西斯保衛中國(guó)西南大後(hòu)方,中國(guó)遠征軍沿著(zhe)滇緬公路向(xiàng)緬甸境内挺進(jìn)。這(zhè)是我國(guó)自1894年甲午戰争以來,中國(guó)軍人首次踏出國(guó)門,赴海外作戰。
1942年5月,中國(guó)遠征軍第一次赴緬甸戰場,後(hòu)被(bèi)日軍切斷歸國(guó)通道(dào),第一路副司令長(cháng)官杜聿明決定率部從野人山撤回雲南,這(zhè)片原始森林遮天蔽日、瘴氣彌漫、毒蟲遍地、野獸肆虐,爲了回到祖國(guó),4萬多遠征軍魂斷野人山,成(chéng)爲世界軍事(shì)史上最悲慘的戰争之一。
任铮是曾經(jīng)活著(zhe)走出野人山而幸存的老兵。時(shí)隔七十多年,每每提及失去的戰友,老人潸然淚下。

以下内容是筆者在2015年5月的采訪
陽光透過(guò)參天的白楊樹,把樹葉投影在明晃晃的柏油馬路上,路邊的操場上活躍著(zhe)孩子們歡快的身影,耳邊回蕩著(zhe)第三套全國(guó)小學(xué)生廣播體操,穿過(guò)兵團綠樹成(chéng)蔭的小路,走進(jìn)第六師五家渠市第一小學(xué)深處的家屬院,抗戰老兵任铮的家就(jiù)在這(zhè)裡(lǐ)。
“你們來的正好(hǎo),再晚來一兩(liǎng)個月,恐怕見不到我了……”。今年96歲的任铮看到記者和志願者一行上門拜訪,面(miàn)帶微笑的招呼著(zhe)。
“哪裡(lǐ),哪裡(lǐ),您至少要活到100歲!”關愛抗戰老兵新疆志願者負責人丁德保(2017年7月22日病逝)托著(zhe)任老的手說(shuō)。
任老不時(shí)的咳嗽、喘息,在兒子的攙扶下,努力從沙發(fā)上顫顫巍巍的站起(qǐ)來,他再次确認了當天的日期:2015年5月24日,他希望,至少要活到日本向(xiàng)中國(guó)投降70周年那天。
鬼子打到了家鄉
任铮的老家在河南溫縣,出自書香門第,回憶抗戰往事(shì),任老心潮澎湃,眼神中閃現出“意氣奮發(fā)少年郎”的模樣(yàng)。

1937年夏天,任铮從縣城中學(xué)畢業後(hòu),來到開(kāi)封,準備繼續求學(xué),但求學(xué)之路被(bèi)戰事(shì)打亂了。
“那時(shí)候,天上是飛機,遠處有煙霧,耳邊還(hái)有槍炮聲,大街上到處都(dōu)是拿著(zhe)行李逃難的人,有好(hǎo)多學(xué)生,有開(kāi)封本地的、還(hái)有東北的、河北的、華北最多,他們往鄱陽湖那邊跑,露宿在岸邊。”
任铮說(shuō),看到這(zhè)種(zhǒng)人心惶惶的緊張局勢,他心裡(lǐ)說(shuō)不出的難受,鬼子來了,無家可歸啊!
當時(shí),開(kāi)封的街頭和學(xué)校到處貼著(zhe)抗日救國(guó)的布告,在一則布告前,任铮看到,國(guó)民革命軍軍事(shì)委員會(huì)通訊兵團訓練大隊招生,任铮毫不猶豫的去報名考試。
考試科目裡(lǐ)還(hái)有英語,因爲當時(shí)通訊語言是由數字和英文組成(chéng)的,任铮說(shuō),多虧自己曾學(xué)過(guò)英語,參加完考試,三四百人隻錄取了六十多人,任铮被(bèi)分到了無線電專業班。
1937年底,任铮和同學(xué)們乘火車從鄭州到武漢漢口的訓練大隊,爲了盡快學(xué)以緻用,學(xué)員們不分晝夜的學(xué)習密碼、密語、發(fā)報。
随著(zhe)戰火四處蔓延,學(xué)員們不斷搬家,先後(hòu)搬到過(guò)湖南長(cháng)沙的中正路、湖南洞庭湖旁的南縣。
1938年夏天,學(xué)員們又轉移到湖南東部的醴陵,訓練大隊的教官都(dōu)是黃埔軍校5、6期畢業的,任铮還(hái)記得當時(shí)的大隊長(cháng)叫(jiào)沈蘊存,中隊長(cháng)姓陳,還(hái)有一個隊長(cháng)叫(jiào)李榮。
學(xué)習了一年的無線電知識後(hòu),任铮于1938年畢業,這(zhè)時(shí)候,訓練大隊已經(jīng)搬到湖南的常德,任铮被(bèi)分到設在湖南南縣的“長(cháng)沙防空司令部”的電台工作,從那時(shí)開(kāi)始,無線電台成(chéng)爲任铮堅守的抗日陣地,“嘀嗒嘀嗒”的莫爾斯電碼,是任铮最親切而熟悉的聲音。
随著(zhe)戰事(shì)變化,任铮又輾轉桂林、到重慶的“防空司令部”,這(zhè)個司令部駐地在四川廣安縣城的圖書館裡(lǐ)面(miàn),任铮記得,對(duì)面(miàn)就(jiù)是楊森公館。
“那時(shí)候,電台的工作特别重要,比方說(shuō),我們接到日軍飛機的飛行信号後(hòu),立即把電報準确的發(fā)到指揮部,指揮部根據信号攻打敵機,所有的命令下達,如何應對(duì),讓哪個部隊出擊,都(dōu)要通過(guò)電台發(fā)出去,這(zhè)關系著(zhe)戰争的勝敗。”
任铮說(shuō),當時(shí),他所在司令部有三、四個報務員,深感責任重大,最擔心的就(jiù)是電報沒(méi)有及時(shí)發(fā)出,贻誤軍情。
随著(zhe)戰事(shì)對(duì)通訊技能(néng)的要求越來越高,1939年,任铮考上了黃埔軍校第17期設在貴陽的通訊兵科獨立第三大隊,在這(zhè)裡(lǐ),任铮又進(jìn)一步學(xué)習了通訊知識。
1941年,任铮畢業後(hòu),被(bèi)分配到國(guó)民革命軍昆明行營通訊指揮部。
遠征撤退 踏向(xiàng)“魔鬼之居”
1942年3月8日,日軍攻占了緬甸的首都(dōu)仰光,切斷了中國(guó)當時(shí)最重要的國(guó)際運輸線路——滇緬公路,威逼印度和中國(guó)的大西南。
爲了保衛滇緬公路,中國(guó)政府抽調了10萬名精兵組成(chéng)遠征軍奔赴緬甸抗日,任铮就(jiù)是這(zhè)10萬名戰士當中的一員。
那一年,任铮被(bèi)派到中國(guó)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(cháng)官羅卓英部任電台台長(cháng),上尉軍銜。司令部在緬甸緬甸中部城鎮眉苗(Maymyo)。
回想遠征緬甸,任铮說(shuō),當時(shí),遠征軍都(dōu)是坐著(zhe)大卡車從中國(guó)到緬甸的,車白天黑夜都(dōu)在開(kāi),不記得開(kāi)了多少天,隻記得到了目的地,看到了大象。
在緬甸,任铮所在的電台主要負責和中國(guó)遠征軍第五軍聯系,當時(shí),杜聿明是中國(guó)遠征軍第一路副司令長(cháng)官兼第五軍軍長(cháng)。
中國(guó)遠征軍在緬甸浴血奮戰,屢挫敵鋒,使日軍受到沉重的打擊。
但後(hòu)來因爲盟軍配合不力,戰鬥失利,遠征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,不得不撤退。可殘忍的日軍欲置遠征軍于死地,切斷了遠征軍的歸國(guó)通道(dào)。
遠征軍的將(jiāng)士們跟随杜聿明將(jiāng)軍選擇了一條無比兇險的回歸之路——穿越一片叫(jiào)做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回到國(guó)境。
對(duì)于這(zhè)條可以回到祖國(guó)的撤退之路,任铮說(shuō),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,雖然,他聽到了很多“進(jìn)野人山必死”的傳言,但野人山到底有可怕,在沒(méi)有進(jìn)入之前,他毫無概念。
“記得,在緬甸的曼德勒(曼德勒是緬甸中部偏北的内陸城市),我們接到命令,把重型武器裝配全部就(jiù)地銷毀,包括我們的電台,那些裝備全部被(bèi)澆上了汽油,火焰燃的老高。”
任铮說(shuō),之所以這(zhè)麼(me)做,據說(shuō),當時(shí)是爲了減輕負重并阻斷日軍的追趕。
滇緬抗戰史專家戈叔亞撰文說(shuō)到部隊進(jìn)入野人山之前的情況:“5月中旬,部隊到達曼德勒以北500多公裡(lǐ)一個村莊,就(jiù)再也沒(méi)公路了。軍長(cháng)下令把重型裝備全部集中銷毀,原來乘坐車輛的1500名重傷病員就(jiù)地安置。”
目前身在安徽合肥的原第五軍新22師衛生兵劉桂英向(xiàng)《瞭望東方周刊》回憶撤退野人山時(shí)說(shuō):
“有軍官把1500個傷兵集中起(qǐ)來問他們,現在我們無路可走了,你們跟我們走也是死路一條,你們自己想個法子處理吧。後(hòu)來傷兵講,你留一點汽油,你們走吧!”
“看到那麼(me)多傷兵自焚而死,我們爬在地上哭起(qǐ)來。”劉桂英說(shuō),“是哭他們,也是哭我們,誰也不知道(dào)自己還(hái)能(néng)不能(néng)活下來。”
邱仲嶽將(jiāng)軍在《抗戰時(shí)期滇印緬作戰(二)——一個老兵的親身經(jīng)曆》中寫道(dào):
“……(一九四二年五月)十四日黃昏時(shí)分,第五軍軍部與第六十五團(新二十二師所部)主力到達莫的林(Mode)宿營,軍直屬部隊及各部隊傷患一千五百餘人進(jìn)駐莫的林東南邊的村子裡(lǐ)……5月16日,第5軍主力縱隊徒步出發(fā),傷病員及辎重全部留在莫的林,或爲戰傷或因重病不能(néng)跟随部隊長(cháng)途跋涉的一千五百餘中華兒女,鹹以生爲中國(guó)人,死爲中華鬼的志節,甯爲烈士死,不做降俘生的決心,慨然于5月21日淩晨一時(shí)引火自焚,含恨而終!
所謂“死路一條”的前路位于緬甸密支那以北胡康河谷一帶的原始森林,位于中印緬交界處,方圓近300公裡(lǐ),遮天蔽日、野獸肆虐,瘴氣彌漫,緬語意爲“魔鬼之居”,因曾有野人出沒(méi),而又被(bèi)當地人稱爲“野人山”。
穿越這(zhè)片原始森林前往中緬邊境,直線距離爲138公裡(lǐ)。
“在進(jìn)入野人山之前,我的一位要從印度撤退的好(hǎo)朋友李國(guó)棟告訴我,野人山特别兇險,他送給了我幾盒火柴、兩(liǎng)雙膠底鞋、一件雨衣。我的一位同學(xué)送給了我治療感染、發(fā)燒、惡性瘧疾等疾病的藥品,我把一支手槍送給了他。
”任铮說(shuō),後(hòu)來看來,就(jiù)是這(zhè)些珍貴的物品救了我命。
據抗戰史專家戈叔亞考證:中國(guó)遠征軍第五軍軍部、新編第二十二師、第九十六師約4萬多人,在遠征軍副司令杜聿明率領下,途經(jīng)野人山撤退。
就(jiù)差一步 我的勤務兵沒(méi)跟上來
“剛進(jìn)山的時(shí)候,還(hái)有工兵在前面(miàn)開(kāi)路,我們跟在後(hòu)面(miàn)走,原始森林的樹高的很,樹葉又大又密,陽光都(dōu)照不進(jìn)來,白天跟晚上一樣(yàng),潮濕、悶熱的透不過(guò)氣,我們幾乎都(dōu)穿著(zhe)草鞋,沒(méi)人戴手表,我手裡(lǐ)有個指北針,我身後(hòu)還(hái)帶著(zhe)四個通訊兵。”任铮回憶說(shuō)。
據史料記載,1942年5月的野人山,悶熱難熬。
從未受過(guò)野外生存與叢林作戰訓練的遠征軍官兵,隻能(néng)靠著(zhe)幾張并不準确的地圖和少數指北針,摸索前進(jìn)。
對(duì)于時(shí)年23歲的任铮來說(shuō),發(fā)現隊伍慢慢潰散的時(shí)候,他已感到不安。
“我們進(jìn)山沒(méi)幾天,就(jiù)開(kāi)始下大雨,雨像石頭一樣(yàng)砸在身上,我立即穿上了雨衣,雨太大了,雨衣都(dōu)穿透了,不一會(huì)就(jiù)在地上積成(chéng)一片水窪地,有些地方開(kāi)始爆發(fā)山洪。
”任铮說(shuō),很快,工兵也沒(méi)法開(kāi)路了,起(qǐ)初,隊伍齊整的在原始森林裡(lǐ)穿行,後(hòu)來,人越走越散。
緬甸的雨季從每年5月中旬開(kāi)始,至10月結束,這(zhè)期間,野人山終日籠罩在傾盆大雨中,雷電閃過(guò),“魔鬼之居”的魔鬼開(kāi)始蘇醒。
1942年5月13日,就(jiù)在杜聿明向(xiàng)擔任斷後(hòu)任務的第九十六師發(fā)出“自行突圍”的命令後(hòu)不久,一直跟随他前進(jìn)的軍部發(fā)報員不慎墜崖身亡,唯一的電台損毀。
進(jìn)入野人山的遠征軍官兵,從此與外界失去了一切聯系。
眼看,進(jìn)山時(shí)帶的糧食越來越少,一股不安的情緒開(kāi)始在官兵中蔓延,随著(zhe)熱帶叢林的雨季到來,山間的小澗也變成(chéng)了洶湧的河流,整個隊伍在沒(méi)完沒(méi)了的暴雨中慢慢潰散。
“在行走的過(guò)程中,一不小心就(jiù)會(huì)喪命。”任铮回憶說(shuō),一路下來,他看到身邊的好(hǎo)多戰友滑進(jìn)河裡(lǐ)就(jiù)沒(méi)起(qǐ)來。
死亡正一步步逼近行進(jìn)中的中國(guó)遠征軍。
任铮回憶說(shuō),身爲電台台長(cháng),原本,他身邊還(hái)帶著(zhe)四個通訊兵,但走著(zhe)走著(zhe),有病死的,有滑進(jìn)沼澤地的、有被(bèi)山洪淹死的,最後(hòu)隻剩下一個兵,他們隻能(néng)一路朝著(zhe)北走,往祖國(guó)的方向(xiàng)前進(jìn)。
“他是我的勤務兵,我的畢業證、黃埔軍校的通訊錄、電碼本都(dōu)在他那,他幫我背著(zhe)行李,四川人,特别能(néng)幹,人也特别好(hǎo),就(jiù)差一步,就(jiù)差一步他就(jiù)跟上我了……”
說(shuō)到這(zhè)時(shí),任铮突然忍不住哽咽,眼淚奪眶而出,那是多年來,任铮最不願意回憶的一幕。
當時(shí),他們在大雨中過(guò)一個窄窄的木橋,任铮剛剛過(guò)了橋,正等著(zhe)他的勤務兵過(guò)橋時(shí),這(zhè)時(shí),工兵團趕來拆橋,以阻斷日軍的追擊,任铮懇求工兵團等等,等他的勤務兵過(guò)來再拆,但軍令如山,他們必須在3分鍾之内拆橋,分分鍾時(shí)間,木橋解體,随著(zhe)翻滾的激流迅速消失……
眼睜睜的看著(zhe)橋沒(méi)了,在悲傷和恍惚中,任铮遠遠的淚别他的勤務兵,心如刀割,他背著(zhe)行李,無助的站在那裡(lǐ),向(xiàng)任铮揮手道(dào)别,“沒(méi)吃、沒(méi)喝、又沒(méi)藥,他過(guò)不來就(jiù)是死啊!”任铮泣不成(chéng)聲。
事(shì)實上,在最後(hòu)活著(zhe)走出野人山的官兵之中,任铮經(jīng)過(guò)多方查找,也沒(méi)有找到他的勤務兵。
一覺醒來 發(fā)現他們都(dōu)死了
淚别了他的勤務兵,任铮悲傷難平,隻剩下他一個人獨行,渴了喝雨水,餓了吃些野果野草,但那些東西很難消化,又餓又累,疲憊不堪。
任铮不知道(dào),更大困難還(hái)在後(hòu)面(miàn),野人山由于不見天日、陰霾潮濕、腐爛氣息令人窒息、漫山遍野的蜈蚣、螞蝗、蛇、以及一些叫(jiào)不出名字的毒蟲到處肆虐著(zhe)、完全不适合人類生存,方圓數百裡(lǐ)都(dōu)是無人區。
最厲害的是螞蟥,“那個螞蝗比中國(guó)的螞蝗大好(hǎo)多,大拇指那麼(me)大,吸了血,有手掌那麼(me)長(cháng),手腕那麼(me)粗,它咬到你,你根本不知道(dào)。”
任铮說(shuō)著(zhe)拍了拍了自己的右腿,行軍休息途中,任铮發(fā)現自己的腿上鼓起(qǐ)來好(hǎo)幾個大包,每個包都(dōu)露出一節螞蝗尾巴,才知道(dào)是螞蝗鑽進(jìn)去了,任铮拼命拽,隻拽斷了一小節。
這(zhè)時(shí),沿路行軍的戰士告訴他,螞蝗鑽進(jìn)肉裡(lǐ)是拔不出來的,要用力拍螞蝗叮咬的部分以及外露的身體,這(zhè)一拍,拍出來七、八條,全都(dōu)吸飽了血出來了,每條都(dōu)有兩(liǎng)根食指那麼(me)粗,任铮說(shuō),至今爲止,他腿上被(bèi)螞蝗鑽過(guò)的地方都(dōu)沒(méi)反應。
熱帶雨林的蟲子是能(néng)吃人的,任铮看到,沿路有很多走不動的官兵,躺在泥水裡(lǐ),瞬間就(jiù)被(bèi)螞蝗和毒蟲包圍。
一路上,任铮看到了太多將(jiāng)士們的屍體,還(hái)看到有病倒的將(jiāng)士自殺的,也許,這(zhè)對(duì)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(néng)的他們來說(shuō),甚至是種(zhǒng)解脫。
“在野人山那種(zhǒng)環境下,心理承受能(néng)力确實是到了極限了。
”任铮說(shuō),沿路看到太多屍體,那種(zhǒng)慘狀沒(méi)法形容,他已經(jīng)不記得自己在山裡(lǐ)走了多少天,隻是一路朝著(zhe)北走。
走著(zhe)走著(zhe),任铮在一片山谷裡(lǐ)看到了房屋,原來,那裡(lǐ)是中國(guó)的華僑,他們在深山裡(lǐ)采玉,他們力勸任铮留下來和他們一起(qǐ)采玉,因爲再往裡(lǐ)走,就(jiù)是死路一條。
“我是一名軍人,我必須遵從軍令回到祖國(guó)。”任铮說(shuō),當時(shí),就(jiù)是這(zhè)個強烈的信念在支配著(zhe)他,臨行前,華僑送給任铮一些幹糧、鐵鍋、火柴、以及一塊像成(chéng)年鴿子一般大小的紅玉,那塊紅玉以備不時(shí)之需。
依然不知道(dào)在深山裡(lǐ)走了多久,當最後(hòu)一點糧食吃完後(hòu),任铮隻能(néng)吃野草充饑,任铮說(shuō),之後(hòu)啥也吃不下,連擡手的力氣都(dōu)沒(méi)有了,他不得不扔掉了那塊在當時(shí)看來,價值連城的紅玉。
走著(zhe)走著(zhe),任铮開(kāi)始發(fā)燒、上吐下瀉、拉出來的都(dōu)是黑水,他知道(dào),自己得了惡性瘧疾,行軍途中,很多戰士都(dōu)是得了這(zhè)種(zhǒng)病死的。
“不到迫不得已,我是舍不得吃那幾片救命藥的,那時(shí)候,我真的感覺自己快死了。”眼前就(jiù)是一片白霧,任铮用樹葉舀了一點雨水,吃下藥片。
極度疲憊之下,任铮看到一個用芭蕉葉搭建的小木棚子,在雨林裡(lǐ),找一塊能(néng)遮擋雨水的地方很不容易,任铮使出渾身力氣爬上棚子,此時(shí),看到上面(miàn)已經(jīng)躺了三、四個戰士,看起(qǐ)來都(dōu)在睡覺,極度疲憊的任铮倒下就(jiù)睡。
“一覺醒來,發(fā)現自己還(hái)活著(zhe),我看他們都(dōu)沒(méi)動,不對(duì)啊,好(hǎo)多大蟲子在往他們身上爬,再看臉,青灰色,還(hái)有黑斑,原來,他們已經(jīng)死了……”
任铮說(shuō),人命還(hái)不如一根草,那一刻,他并不感到恐懼,沿途看到太多戰士們的屍體,有些被(bèi)螞蝗吸血、螞蟻啃噬、大雨侵蝕後(hòu),數小時(shí)後(hòu)就(jiù)變化了白骨,此刻,對(duì)于任铮來說(shuō),最大的恐懼是,怎麼(me)活下去?
腳趾頭插進(jìn)石頭縫 翻越高山邁向(xiàng)國(guó)境
暴雨、饑餓、沼澤、毒蟲、死亡、深陷野人山的任铮感到前路絕望。
杜聿明曾在回憶錄《中國(guó)遠征軍入緬對(duì)日作戰述略》中寫到野人山撤退:
“……洪水洶湧,既不能(néng)徒涉,也無法架橋擺渡,我工兵紮制的無數木筏皆被(bèi)洪水沖走,有的連人也沖沒(méi)……螞蝗叮咬,破傷風病随之而來,瘧疾、回歸熱以及其他傳染病也大爲流行……官兵死亡累累,前後(hòu)相繼,沿途屍骨遍野,慘絕人寰。”
野人山的生水是不能(néng)喝的,喝了就(jiù)會(huì)死,但對(duì)于極度饑餓、且沒(méi)有原始叢林生存經(jīng)驗的中國(guó)遠征軍來說(shuō),饑不擇食,很多戰士在喝了野人山的生水後(hòu)腹瀉、嘔吐,直到倒下,再沒(méi)有爬起(qǐ)來。
“一路走來,屍體遍地,每具屍體上都(dōu)是成(chéng)群結隊、大多出奇的蟲子。”
任铮說(shuō),有一天,終于不下雨了,很難得的看到了太陽,他走到一個河谷邊,躺在一塊大石頭上休息,不知不覺睡了過(guò)去,一覺醒來,突然發(fā)現自己的左腿泡在水裡(lǐ),整個左腿泡漲了,腫了好(hǎo)大一圈。
“太累了,睡著(zhe)的時(shí)候,腿蕩到了水裡(lǐ)都(dōu)不知道(dào)。”任铮說(shuō),至今爲止,他的左腿常常感到麻木。
在艱難的跋涉中,同鄉送他的膠底鞋全都(dōu)走的破爛不堪,直到走沒(méi)了,最後(hòu),任铮隻能(néng)光腳前行,順著(zhe)指北針,任铮開(kāi)始翻越一座高山。
“那山很陡,我把腳趾頭插到石頭縫裡(lǐ),一步一步往上爬的,退路就(jiù)是死,我隻能(néng)前進(jìn)。”
任铮說(shuō),越往上爬越冷,他後(hòu)來才知道(dào),翻越的那個山叫(jiào)——高黎貢山,他的腳已經(jīng)邁到了國(guó)境。
高黎貢山位于雲南西部怒江大峽谷,坐落于怒江西岸,是橫斷山脈中最西部的山脈,北連青藏高原,平均海拔3500米,是中緬邊境上的一道(dào)天然屏障。
然而,高黎貢山的山頂常年積雪,由于中國(guó)遠征軍還(hái)是夏季裝備,缺乏禦寒的冬衣,成(chéng)百上千的遠征軍千辛萬苦的穿越了野人山之後(hòu),卻在寒冷的高黎貢山被(bèi)活活凍死。
“我用最後(hòu)的力氣爬到山頂的時(shí)候,看到了白雪,可我身上,隻挂著(zhe)幾縷破布,凍得要命,我不能(néng)停,停下來就(jiù)會(huì)凍死。”
任铮說(shuō),寒夜裡(lǐ),他光著(zhe)腳在雪地裡(lǐ)不知走了多久,突然看到了火光,是從一個洞穴裡(lǐ)發(fā)出來的光,走進(jìn)一看,有四、五個戰士圍坐在一起(qǐ)烤火取暖,他們看到任铮,那種(zhǒng)無法言說(shuō)的表情令任铮終身難忘,和戰友們擠在一起(qǐ)烤火的時(shí)候,任铮忍不住哭了,絕處逢生啊!
後(hòu)來,殘兵們結伴回到了雲南,然而,活著(zhe)走出野人山的官兵們并不感到欣喜,那些逝去的將(jiāng)士是他們的朋友、同鄉,是曾經(jīng)生死與同的親密戰友。
1942年8月底,随著(zhe)第九十六師最後(hòu)一批殘兵翻越高黎貢山,抵達雲南劍川,中國(guó)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至此結束。
根據杜聿明將(jiāng)軍的粗略計算,中國(guó)遠征軍10萬人,生還(hái)者僅有4萬,戰犧牲有1萬多人,也就(jiù)是說(shuō),有4萬將(jiāng)士是在撤退途中非戰鬥犧牲的,他們的屍骨至今還(hái)在野人山的叢山峻嶺之中。
“同路的好(hǎo)朋友,好(hǎo)同學(xué)都(dōu)死了,隻有我一個人活著(zhe)回來,我難受啊!”任铮說(shuō),在雲南的兵站,當他把那身穿了幾個月、已變成(chéng)幾縷破布的衣服脫下來的時(shí)候,連自己都(dōu)不認識自己了,全身都(dōu)是膿瘡和密密麻麻的虱子,在當地治療的很久,任铮身上的膿瘡才勉強愈合。
翻越野人山對(duì)任铮來說(shuō),更難治愈的是心理創傷。
野人山大撤退,導緻中國(guó)遠征軍走向(xiàng)慘重的毀滅之路,全程穿越野人山的將(jiāng)士死亡率接近90%,杜聿明本人也承認,這(zhè)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。
身體逐漸康複後(hòu),任铮被(bèi)調到“交通部公路總局無線電總台”第二台工作,脫離軍隊。
先當報務員,後(hòu)當台長(cháng),同時(shí)兼任《大公報》電務員,負責收集日本,美國(guó)的電訊。

抗戰勝利後(hòu),任铮回到重慶通訊兵三團,1949年在重慶起(qǐ)義。
後(hòu)來,任铮在解放軍西南通訊兵學(xué)校當教員,1952年轉業回河南老家種(zhǒng)地,教書,之後(hòu)在當地成(chéng)立了“童聲豫劇團”。
1959年,新疆生産兵團到河南招收豫劇團,任铮和他的豫劇團,全團81人被(bèi)招錄到了新疆,定居新疆後(hòu),改名爲“新疆軍區生産建設兵團政治部童聲豫劇團”,任铮擔任編劇。
他編劇的劇本以弘揚民族文化爲藝術宗旨,在整理和改變傳統戲、新編曆史劇、創作現代戲等方面(miàn)做出了巨大成(chéng)績,連文革期間還(hái)在演出他編的劇本。
豫劇團後(hòu)更名爲“新疆生産建設兵團豫劇團”,任铮一直在豫劇團工作,直到退休。
如今,晚年的任铮住在兒子家,他極少向(xiàng)人提起(qǐ)那段抗戰經(jīng)曆,哪怕是兒子。
“這(zhè)些年,我一閉上眼睛,就(jiù)看到野人山了,我的勤務兵,多好(hǎo)的小夥子,我是踩著(zhe)他們的命活出來的……”
七十多年來,這(zhè)一幕在任铮的腦海裡(lǐ)反複上演,戰争的殘酷記憶在他的心裡(lǐ)生根發(fā)芽,而這(zhè)絲毫不會(huì)因爲歲月的增長(cháng)而消退,反而日久彌新。

采訪臨近結束時(shí),任铮爲我們唱起(qǐ)了《黃埔軍校軍歌》,用手拍打著(zhe)膝蓋,聲音铿锵有力:
怒潮澎湃,黨旗飛舞,這(zhè)是革命的黃埔。主義須貫徹,紀律莫放松,預備作奮鬥的先鋒。打條血路,引導被(bèi)壓迫民衆,攜著(zhe)手,向(xiàng)前行,路不遠,莫要驚,親愛精誠,繼續永守……
文/圖: 李萍
注:其中老照片爲翻拍
老兵唱黃埔校歌的視頻拍攝者爲
志願者:丁德保 (已故)
征稿公告
老兵口述
抗戰親曆故事(shì)
聽父輩講述抗戰歲月
志願者手記
抗戰曆史研究
一張老照片的故事(shì)
......
(一經(jīng)采用,送上精美禮品)
期待你的來稿:ljian@szlongyue.org